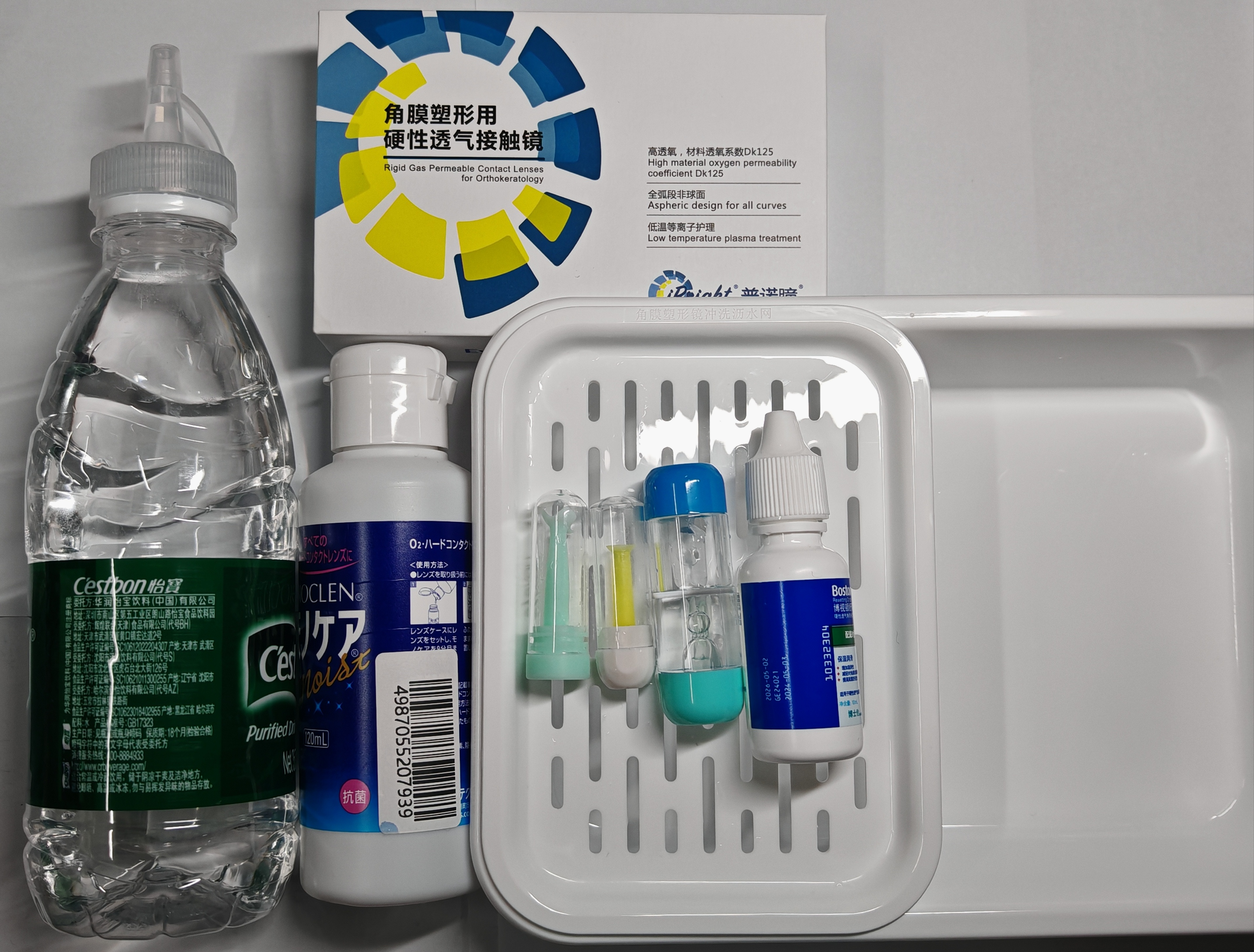貝木泥舟全セリフ1
♦︎ 僞物語
【第3話 かれんビー其ノ参】
(06:46)
ふぅむ、お前はこの家の子供かな?
あぁ、すまない、名乗り忘れた。
見ず知らずの人間に対するその警戒はひどく正しい。大切にするがいい。
俺は貝木という。
そう、貝塚の貝に枯れ木の木だ。
そこまで説明しなくていい。
それは聞いたばかりの名だ。
ただし俺が枯れ木だとすればお前は若木なのだろうがな。
ふぅ、お前は最近の若者にしては礼儀正しいな。それに気遣いのできる男だ。面白い。
ただし、俺に対してはそこまでの気遣いは無用だ。
この家にも特に用があった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
ただし、臥煙の女の忘れ形見がここで暮らしているという話を聞いてしまったのでな。
何をするわけでもないが少し様子を見てみようと思っただけだ。
しかし無駄足だったな。ほとんどオーラを感じない。およそ1/3といったところだな。
これならば放置しておいていいだろう。いや、放置しておくしかあるまい。
残念ながら金にはならん。
今回の件から俺が得るべき教訓は、真実などたとえ思い通りであったところで場合によってはくだ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だ。
【第5話 かれんビー其ノ伍】
(05:20)
ようこそお嬢さん。俺は貝木。貝塚の貝に枯れ木の木だ。
お前の名前を聞こうか。
良い名だな。親に感謝しておけ。
それでお前はどちらだ?
おまじないを教えてほしいのか?それともおまじないを解いてほしいのか?
前者なら1万。後者なら2万だ。
殴りに来た…ほぅ、つまり俺を嘘のメールで呼び出し罠に嵌めたということか。
なるほど、みごとな手際だ。
もっとも、お前の手柄とは思えないな。
お前のような短絡的な人間が俺の地点までたどり着けるとは思えない。
そうはいないはずなんだ。
こうして俺と対面できるところまで到着するなどやや常軌を逸している。
何が迷惑だ?
俺はお前たちの望んだ物を売り渡しているだけだぞ?その後は自己責任だろう?
どういうつもりか?深い問いだなぁ。
しかし残念なことに俺は深い問いに対して浅い答えを返すことになる。
それはもちろん金のためだ。
世の中というのは金がすべてだからな。
お前はどうやら下らん正義感でここに来たようだが、惜しいことをしたものだ。
その行為、依頼人から10万は取れる。
今回の件からお前が得るべき教訓は、ただ働きは割に合わない、だ。
そうか…誰かに頼まれておくべきだったなぁ。
若いなぁ。決して羨ましいとは思わないが。
どうした?震えているぞ。阿良々木。
阿良々木、お前は俺の目的を聞いたな?
今度はお前の番だ。お前の目的は何なのだ?
殴るだけか?
暴力かぁ。
これでも大人だ。それにアコギな商売になるのは当たり前だ。俺は詐欺師だからな。
別に。子供が相手だから騙しやすい。それだけのことだ。
しかし阿良々木よ、俺のやっている事を辞めさせたければ殴るのも蹴るのもとりあえずは無駄だな。
それより金を持ってくるのが手っ取り早い。
この件に関する俺の目標額は300万だ。
根を張るまでに2か月以上かけている。最低でもそれくらいは儲けないと割に合わない。
あいにくだがこれでも人間だよ。
大切なものを命を賭して守りたいと思うただの人間だ。
お前は善行を積むことで心を満たし、俺は悪行を積むことで貯金通帳を満たす。
そこにどれほどの違いがある?
そう、違いなどない。
お前はお前の行為によって誰かを幸せにするかもしれない。
しかしそれは、俺が稼いだ金を浪費して資本主義経済を潤すのと何ら変わりはないのだ。
今回の件からお前が得るべき教訓は、正義で解決しないことがないよう、金で解決しないこともないということだ。
俺の被害にあった連中にしてもそうだろう。
連中は俺に金を払った。それは取引の対価として金を認めたということだ。
お前だってそうだろう?阿良々木。それともお前はそのジャージを買う時金を払わなかったのか?
殴られたくはない。蹴られたくもないなぁ。痛いのは嫌いだ。
だから、お前には蜂をプレゼントしよう。
効果覿面だな。随分と思い込みの激しいタイプと言える。
今回の件からお前が得るべき教訓は、人を見たら詐欺師と思えということだ。
人を疑うということを少しは覚えるのだな。
俺が許しを請うとでも思ったのか?だとすれば愚かだ。
俺を改心させたくば金を積め。1,000万円から議論してやろう。
悪いことだよ。もちろん有料だ。金は貰う。4,000円か。まぁいいだろう。
さっきの話の分はサービスしておく。
電車台として小銭くらいはぉ…なんだ定期券があるのか。ならば小銭も不要だな。
少しすれば毒が定着し動けるようにはなる。携帯を使って助けを呼ぶことを勧めるよ。
俺はその間にトンズラするとしよう。
もちろん商売は続けさせてもらうが、しかし、直接顧客と会うのはこれからは避けた方がよさそうだな。
良い教訓になった。ではさらばだ。
【第7話 かれんビー其ノ漆】
(09:45)
(00:00)(11:49 買手機預告)
お前は臥煙の忘れ形見の家の前であったかな?
妹の意思返しか。今どき随分と珍しい漢気のある子供だ。
しかし魅力がなくなったなぁ戦場ヶ原。普通の女子になっている。
俺は会いたくなかった。普通の女子になったお前になど、決して。
前に合った時のお前は闇のように輝いていたぞ。いや、悟っていたと言うべきなのか、実に騙し甲斐があった。
よせ、話し合おう。俺は話を聞く。その為に来た。
お前たちも話をしに来たのであろう?違うか?
よろしい、わかった。もう中学生をたぶらかすのは辞めよう。
これ以上のおまじないを広める事はもうしない。
あの元気のいいお嬢さん、お前の妹の事なら心配することはない、阿良々木。
アレは瞬間催眠と言うやつだな。
崩れている体調も三日もすれば治る。
それから戦場ヶ原、お前の母親の事については正式に謝罪しよう。
お前の父親から巻き上げた金銭にしてもできる限りの返却に努めよう。
そうか。そういえば謝罪の言葉をまだ口にしていなかったな。それに、命乞いの言葉もだ。
悪かったな、実にすまない、お前たち、とても反省している。悔いるばかりだ。
そうかもしれない。
そのようだな。そしてその辺りが普通になったと言っている。
昔のお前なら絶対に我慢などしなかった。
そうかぁ、それは助かる。
俺は金遣いが荒くてな。貯えなどなどほとんどない。
お前に金を返す為、新たな詐欺を働か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ところだった。
わかった。
どうした阿良々木?なぜ俺をそんな目で見る?
お前は俺に妹を痛められている。もっと恨みに満ちた視線をこそ俺に向けるべきではないのか?
それは違う。あの娘のミスは一人で俺に会いに来たことだ。
俺をつるし上げたかったのなら、今お前たちがそうしている様に複数名で来るべきだった。
それ以外の点においてあの娘は概ね正しい。
それとも阿良々木、お前はあの娘を愚かだと断定し、あの娘を愚かだと否定するのか?
強くはない、と?確かに強くはない。
だがあの娘のやさしさは否定するべきではなかろう。
それに、ああいう娘がいないと、詐欺師としては商売あがったりだ。
戦場ヶ原、お前は俺を誤解しているな。
いや、誤解ではなくむしろ過大評価だと言うべきか。
お前が敵視するこの俺は、ただのさえない中年だよ。
詐欺師としても至極小物のわびしい人間だ。それともお前には俺が化け物にでも見えたか?
そう、その通り。俺は偽物だ。
俺は大した人間ではない。そしてお前も大した人間ではない。
俺は劇的ではなく、お前も劇的ではない。
阿良々木、お前はどうなのかな?
俺はお前に質問してみたい。お前の人生は劇的か?悲劇的か?喜劇的か?歌劇的か?
お前の影からはどうも嫌な気配を感じるのだが。
それにどうやら妹の被害を半分ほど引き受けているようだ。正気の沙汰ではない。
金ももらわずよくそんなリスキーな真似をする。
どっちとは?
ふん。これは思いのほか下らん質問が来たな。
興が削がれる。阿良々木、例えばお前は幽霊を信じるか?
幽霊を信じはしないが、幽霊を怖がるという人間の心理は分かるだろう。
俺もそれと似たようなものだ。だからお前の質問にはこう答えよう。
怪異など俺は知らない。しかし、怪異を知る者を俺は知っている。それだけのことだ。
正確には、怪異を知ると思い込んでいる者を知っているだけなのだがな。
囲い火蜂。囲い火蜂の事をお前は知っているか?
正解だ。ただし間違っている。
囲い火蜂は江戸時代に著された文献、東方乱(みだれ)図鑑の15段に記載されている怪異談だ。
しかし根本的な話、室町時代にそんな病が流行っていたという事実はない。
偽史というやつだ。その作者の書いたデタラメを愚かにも後の世の人間が信じてしまったのだよ。
お?
当然だ。囲い火蜂など存在しない。怪異など存在しない。
ならばその被害も存在してはならない。
お前たちがあると思うから、そこにある気がしているだけだ。
ハッキリ言おう。お前たちの思い込みに俺を付き合わせるな。迷惑だ。
ましてお前が半分引き受けているのだからな。
完治まで3日もかからないかもしれない。
どんな方法をとったかは知らないが大したものだ。
だがそれだけに阿良々木よぅ、お前と俺とは相容れないのだろうな。
水と油どころではない。火と油だ。
さて、お互い火という感じではなさそうだが。
ではルビジウムと水と言い換えようかな。
この場合俺がルビジウムだ。
おわ?
酷い事をする。
これでは中学生の子供たちに対するケアもできないな。
顧客の連絡先もわから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だから。
騙すだろうな。俺は詐欺師だ。償いだって嘘でする。お前らは理解したくないだろうがな。
俺にとって金儲けとは損得ではないのだ。
俺のそういうところがどうなんだ?
無言か。本当につまらん女に育ったな、戦場ヶ原。
昔のお前は劇的ではなかったにしろ最高ではあったぞ。今のお前は本当につまらん。
贅肉にまみれ、重くなったな。
ぉっおお、なんと。お前たちはそういう関係か。
そうかそうか、そういうことか。ならばもう何も言うまい。馬に蹴られて死ぬ気もない。
それでいいと言うならば償いもしない。
俺もあえて金にならない事はしたくないからな。
この街から黙って消えよう。明日には俺はもういない。それでいいだろう?戦場ヶ原。
そうそう戦場ヶ原、良い事を教えておいてやろう。
かつてお前に乱暴しようとした男の話だ。
車に轢かれて死んだらしいぞ。
お前とは何の関係もない場所で、お前とは何の関係もなく、そして何のドラマもなく。
お前が気に病んでいる過去などその程度だ。
決別するだけの価値もない。
今回の件からお前が得るべき教訓は、人生に劇的なことを期待し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だ。
戦場ヶ原、事を平面的に捉えるな。
ひょっとしたら俺がお前の事を忘れていたという事の方が嘘なのかもしれないだろう。
嘘だろうとどうだろうと、所詮この世に真実など存在しない。
心配するな。お前がかつて俺に惚れていた事など別に浮気には値しない。
今の恋人に対し誠実であろうとするあまり、俺を逆恨みされても困る。
繰り返そう、過去は所詮過去にすぎん。
越える事にも追いつく事にも価値はない。
お前ともあろう女が下らん想いに縛られるな。
せいぜいそこの男と幸せに過ごせ。さらばだ。
【第10話 つきひフェニックス其ノ參】
(00:20)
いわゆる野暮用だよ。ただの下らん野暮用だ。
阿良々木、お前が気にするようなことではない。
いずれすぐに消えてやる。
そう急かすなよ。
お前達に2度と会いたくないのは俺の側も同じだよ。
お前達のせいで俺は大損こいたんだからな。
知りたいか?教えてやる。金を払え。
どれ、ん、ま、いいだろう。
阿良々木、お前と戦場ヶ原、若い男女の前途を祝する意味でこの程度のはした金で許してやろう。
あいつらは専門家だよ。
俺と同じゴーストバスターだ。
もっとも、俺が偽物であるのに対して、あいつらは本物だ。
俺が詐欺師なら、あいつらは陰陽師だ。
勢いで”ら”などと言ってしまったが、厳密には陰陽師は影縫の方で斧乃木はあくまで式神だそうだがな。
なぜそう思う?
名を知っているだけだ。
影縫の方は業界ではそこそこの有名人だからな。
影縫余弦と斧乃木余接、あくなき現代の陰陽師。
なぁ阿良々木よ、専門家とはいえ連中の専門は非常に狭い。
あのツーマンセルの専門は不死身の怪異なんだぜ。
【第11話 つきひフェニックス其ノ肆】
影縫轉述:
(本物とそれと全く同じ区別のつかんような偽物とどっちの方が価値があると思う?)
(偽物の方が圧倒的に価値がある。
そこに本物になるという意思があるだけ、偽物の方が本物よりも本物だ。)
♦︎ 花物語
【第28/2話 するがデビル 其ノ貳】
(07:13)
やっと会えたな。臥煙の忘れ形見。
ほぅ、俺を知っているか。
そうか、阿良々木や戦場ヶ原辺りから聞いたのかな。それなら話は早い。
この件から俺が得るべき教訓は、人の縁とはどこでどう役に立ってくるとは分かったもの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な。
おいおいちょっと待てよ、臥煙の忘れ形見。
俺はお前を待って…
いきなり走るなよぅ、危険だぞ。
だからグラウンドでもない場所でいきなり走るなよぅ。
お転婆なガキだな。それこそ転ぶぞ。気を付けろ。
たく、仕方ねぇな。お前それでも臥煙の忘れ形見かよ。
なんだよ、凄え顔してるな、お前。逃げるなよ。
さっきも言ったが、ようやく会えたんだ。
なにせ俺は戦場ヶ原と阿良々木にあの街から締め出しをくらちまっているからな。
だから去年の夏からこっち、お前が街から出るのをずっと待っていたんだ。
そうだ、いや嘘だけどな。
どうした?付いて来いよ。
あぁ、それでさっきいきなり駆け出したのか。
親切な先輩を持ったものだな。
しかしお前が逃げ切れなかった時のパターンを考えておいてくれなかったのは不親切とも言える。
この件からお前が得るべき教訓は、逃げるだけでは解決しない物事もあるということだ。
心配するな、お前を騙すつもりも利用するつもりもない。
俺はお前に話があるだけだよ、臥煙の忘れ形見。
こんな人通りの多い駅前で立ち話でするような話じゃないからその辺の喫茶店にでも入ろうと誘っているだけだ。
本来そんな事は天変地異が起ころうともあり得ないのだが、今日に限りお前が相手に限り、特別だ。
お茶くらい奢ってやる。
予約した貝木だ。
ほれ、肉を食え肉を。焼き肉屋で野菜とか頼む必要はねえんだよ。
野菜が食いたきゃ焼き野菜屋に行けばいいんだ。
任せろ、俺が焼いてやる。
若いうちはとりあえず肉だ。
肉を食っていれば人間は幸せになれるぜ、臥煙の忘れ形見。
まぁ若造でも老人でも人生に悩みは尽きないが、しかし美味しい肉を食えばそんな悩みは全て解決するのさ。
ふん、なるほど。その通りだな。
しかしお前の事を神原と呼ぶのは業腹だ。
その苗字は臥煙のものではないからな。
駿河と呼ぶことになるがそれで良いのか?
そうか。では駿河、早く肉を食え。肉は熱いうちが勝負だ。
ほぅ、駿河は右利きか。臥煙は左利きだったがな。
いや、左手を怪我しているからあえて右手を使っているのかな。
他に何か食べたい肉はないか。
あぁ、まぁそうだな。
うん、そういえば、そうだった。
既に気付いているとは思うが、駿河、俺はお前の母親を知っている。
えぇっと、というかお前、去年の8月にお前の叔母って奴と会ってないか?
ほら、臥煙伊豆湖。
そうか、あの女らしいな。
俺は伊豆湖とはそりが合わなかったが、お前の母親には何度か世話になったんだよ。
お前よりもガキだった頃にひょんなことで知り合ってな。
付き合いは大学生の頃まで続いたが、まぁ家庭教師みたいなもんか。
俺は臥煙から頼まれてたんだよ。
もしも私の身に何かあったら娘を気にかけてやってくれ、と。
臥煙が死んだと聞いたのは最近の話さ。
その忘れ形見となった一人娘は、父方の祖父母に引き取られたという話もな。
それは逆だな。
ついでなのはお前の方だった。
臥煙からは金も貰ってないのに俺がそこまでする理由はない。
事のついでに、ふと見てやろうとしただけだ。
ん?コレだからガキは、なんでも恋愛に絡めたがる。
下らねぇ。
しかしまぁ、褒めてやってもいい洞察力ではある。
いや、概ね当たりだよ。
そう、大学生の頃にな、俺はお前の母親に憧れていた。
いい女だったぜ。まぁ当時俺には俺でちゃんと恋人がいたから関係を持ったなんて事はねえよ。
安心しとけ。ただの思い出だ、思い出。一銭の価値もない思い出。
さぁな。なにせ俺が臥煙を知っているのは15年くらい前の話だ。
似てるか似ていないかと言えば親子なんだから似ているんだろうが、
俺の方が臥煙の顔をうろ覚えだ。
だから、冷たいんだよ俺は。
まぁ、なんにしても駿河、臥煙の忘れ形見であるお前が元気そうで良かったぜ。
その左手だって本当は怪我なんてしてないんだろ?
まぁそんな機会はないと思うが何か困った事があれば連絡しろ。
一応はあの女との約束だ。気に掛けてやろう。
いや、お前は騙さねえよ。
先輩を尊敬しているんだな、駿河。
お前はそうやって気を張って俺の事を嫌いでい続けないと、俺に対して否定的な気持ちを持ち続けないと大好きな先輩達に対して不実を働いている気分になる訳だ。
だが無理だぜ。俺はお前を騙さないし、俺はお前に害をなすつもりはない。
だからお前は俺を嫌いになれない。
好きな奴がお前の事を好きになってくるとは限らないことと同様、嫌いな奴がお前の事を嫌いになってく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んだよ。
そして嫌われてくれるとさえ限らないんだ。
漫画とかのキャラクターじゃねえんだぜ?
嫌なだけの人間はいない。悪いだけの人間はいない。
どの方向から見ても同じ性格の奴はいないし、どの時点でも同じ性格の奴はいない。
お前は走るのが得意な様だが、しかし常に走りはしないだろう?
歩きもすれば、寝もするだろう。同じことだ。
俺は金が大好きだが、その金を使いもする。
特に思い入れがなくても、誰かに親切にすることもあるさ。
あぁ、大抵の奴なら騙してやるぜ。
どうした?肉を食う手が止まっているぞ。
肉肉、肉肉肉だ。
牛・牛・豚・鶏・牛・内臓・内臓の順で食え。
お前は少し痩せ気味だぞ。肉を食ってブクブク太れ。
まぁ俺に頼らずに済むのなら頼らない方が良いよ。それは確かだ。
けれど猿の手に頼るよりはまだ俺の手に頼る方がマシだろうぜ。
託されてるだろう?母親から。猿の手のミイラ。
念の為に言っておくが、絶対に使うなよ。
近々お前の前に回収業者が現れるだろうからソイツにくれてやれ。
あぁ、いわゆるコレクター、収集家って奴だな。
悪魔のパーツを全身分集めようという奴がいる。
ソイツはお前から猿の手を奪おうとするはずだ。
悪い事は言わん。現れたらさっさとくれてやれ。
さて、俺の陰気な面を見ながらじゃあどうやら食事も捗らんようだ。
俺はもう帰るからよ、後はゆっくりやってろ。
あと、2皿3皿追加注文しろよ。
肉、肉を食え、肉だ。じゃあな。
ん?
どうしたよ?なんだ?俺に惚れたのか?
聞いていたからさ。お前の友達に。
日傘?そんな名前じゃなかったな、あのガキは。
沼地、沼地蠟花。そう、確かそんな名前だった。
♦︎ 恋物語 前篇
【第21話 ひたぎエンド 其ノ壹】
人は真実を知りたがる。あるいは自分の知っているものを真実だと思いたがる。
つまり、真実が何かなどは二の次なのだ。
何が真実で何が嘘なのか気を付けながら、つまりは常に疑いながら、心に鬼を飼いながら読むことをお勧めする。
もっとも、その時点で俺の罠に嵌っているかもしれないと付け加えることを忘れる俺でもないが。
ではでは虚実入り混じる描写、ある事ない事織り交ぜて、戦場ヶ原ひたぎと阿良々木暦の恋物語を語らせてもらおう。
真実かどうかは保証しないが、クオリティは保証する。
最後に読者全員がざまぁみろと思えるような結末があの二人に訪れればいいと、心の底から俺は思う。
俺に心があればだが。俺なんて奴がいればだが。
それでは面白おかしく最後の物語を始めよう。
なんてこれももちろん嘘かもしれないぜ。
その日俺は日本京都府京都市のとある有名な神社に来ていた。元旦である。
神社に来ているのは元旦ゆえの二年参りという訳だ。というのは嘘である。
遊び半分で神社を訪れ、命よりも大事な金をゴミか何かのように放り投げる人間を観察する為に、
そういう人間の生態を研究する為に、俺は神社にやってきたのだ。
という話をすればそれっぽいのかもしれないが、実際は全然別の理由かもしれない。
本当は今年一年の健康を、あるいは良縁でも祈りに行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
とか俺に関してかもしれないを追求すればキリがないかもしれない。
は?
私は鈴木と言います。
首輪につける鈴に、木で鼻を括るの木、と書いて鈴木です。
失礼ですがどちらにお掛けですか?
戦場ヶ原、まるきり覚えのない名前ですが…。
戦沼ヶ原?誰だ?いや、どこだ?
沖縄。沖縄の那覇市の喫茶店だ。喫茶店でモーニングを食べている。
ヨロシクお願いする。
とにかく、俺はその日自分の吐いたくだらない嘘の為に沖縄へ行かなくてはなら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だった。
あいつに誰だかわからないがあの娘に騙したいと思うような人間がいるのか
詐欺の被害にあい酷い目にあった人間が、同じように人を騙そうなどと思うものなのか。興味深い。
好奇の目で見ざるを得ない。
そんな彼女が、誰だか知らないがとにかく彼女が他ならぬこの俺に詐欺の片棒を担げと言うのだから不自然極まりない。
その点においては違和感しかない。
あえて別の言葉を探せば違和感ではなく嫌な予感というやつだ。
貝木とは誰でしょう?私は鈴木と言います、戦沼ヶ原さん。
戦沼ヶ原さん、実は既に空港の傍まで戦沼ヶ原さんを迎えに上がっております。
クライアントにわざわざご足労頂いたのですから、それが当然だと。
ですから空港のロビー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何を仰っているのか全く意味が分かりませんね。
分かりました。では、そうしましょう。
いえいえ、空港内の喫茶店全てを巡って、必ずこちらからお声掛け致しますので
戦沼ヶ原様は優雅に紅茶でも飲みながらお待ちくだされば。
へへっ、よし勝った。
ホットコーヒーを。それからこちらの女性にオレンジジュースをもう1杯。
久しぶりだな、戦沼ヶ原。
お前から俺に連絡してくるとはな。どうした?何かあったのか?
漠然と言われても困るな。もちろん俺に騙せない人間などいないが。
しかし、具体的な話を聞かせてもらえない限り返事はできない。
なんだぁそりゃ?償いというやつか?
昔お前を酷い目に合わせたのだから、その埋め合わせをしろとでも?
そりゃあ何と言うか、大きくなったなぁ戦場ヶ原、おっぱい以外も。
そう、それは重畳、お安くないな。
そんな風に自分の行動を制約されるのはいささか嫌気がさすな。
なんなら今すぐ俺は帰ってもいいんだ。
刺されるのは嫌だな。
仕方がない。話くらいは聞いてやろう。
言うことを聞いてやるかどうかは分からないが、聞かせろよ戦場ヶ原。
お前、俺にどこの誰を騙して欲しいと言うんだ?
なんとなく口ぶりからすると、俺の知っている人間ぽいが。
阿良々木は知っているのか?
お前がこうして元旦から俺に会っていることを?
そもそも彼氏彼女というものは元旦に一緒に初詣をするものではないのか?
お金をゴミのように手荒く放り投げながら。
ふん、知らない。つまり、つまり阿良々木に秘密で俺に会いに来たというワケか。
いや、別に。で、なんだ?阿良々木との高校生活最後の貴重な冬休みの時間を費やしてまで、
つまり、彼氏に秘密を作ってまでお前は詐欺の共犯者になろうとでもいうのか?
その千石撫子というのが誰だかは知らないが恋敵か何かか?
ふーん。まぁ阿良々木の学力がどの程度かは知らないが、お前がつきっきりで教えてやっているのであればきっと問題ないのだろう。
春からは2人とも大学生ということだ。
うん?
あ?
ほぅ?
つまりお前と阿良々木が何かで恨みを買って、その千石撫子とかいう奴に殺されそうになっているから
ソイツをなんとか言いくるめてほしいということか。
ふん、しかし殺されるとは穏やかじゃないな。
いいだろう、聞くだけならな。
話せばそれで楽になってスッキリ解決し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もあるだろうし。
ほぅ面白いな。人間でなければなんだ?
神様になったというのは、お前と同じ奇病にか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で良いのかな?
やぁそんな神社は知らんな。
しかしそこに祀られているというのはハッキリ言って意味が分からないが、
つまりそれは千石撫子は現在生き神として信仰を受け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か?
生き神とか現人神とか。
ふん。
その子はどうしてそんな奇病にかかったんだ?
話を聞いているとどうやらお前の同級生のようだが。
中学何年生だ?
ん?
ん、あの街、お前の住むあの街に住んでいる中学生だということは
つまり、俺が去年騙した中学生の中の1人というワケだな?
ほぅ、詐欺による連鎖倒産の様なものか。そうだな。
詐欺は連鎖的に被害を生むから個人の範囲に収まらない社会悪なのだよな。
すいません、この子がオレンジジュースをこぼしてしまいました。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が同じ物をもう1杯お願いします。
案ずるな、大人は子供の粗相にいちいち腹を立てたりしない。
感じる、感じる。責任感に押し潰されて死にそうだよ。
その償いだけは絶対にしなくちゃあな。万難を排して償うよ。
教えてくれ戦場ヶ原、俺は何をすればいいんだ?
その言葉を俺は2年前にも聞いた。
同じセリフを同じ相手に言うのは一体どんな気持ちなのだろう?
どんな気持ちなのだろう?
助ける、俺が戦場ヶ原を。そして阿良々木を助ける。
なんだかその文言は悪い冗談のようだった。
そして俺は悪い冗談が嫌いではないので、結構愉快な気持ちになった。
神様を騙せというのか?俺に。
あるねぇ。というよりたかが神様を騙すのに自身なんかいらん。
俺に騙せない相手はいない。
できるな。
余裕だ。ロリ奴隷があと5人増えても全然余裕だ。
ただしそれはできるというだけの事でやるかどうかは別問題だ。
そもそも俺が人を騙すのは金のためだ。
一文の得にもならないのに、どうして俺はその千石撫子を騙さ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のだ?
例え神様だとしても中学生を騙すなど良心が痛んで仕方がないじゃないか。
ふん、もちろんと言うほどお前に支払い能力があるとは思えないが。
だったら今回も同じ額を払って忍野に頼むんだな。
羽川?
なんだ?
それは天地がひっくり返ってもあり得ない。
まぁ、足りないな。
さすがに命がかかると必死だな。
それとも恋人の命が大事という感情なのかな。
もしも払える限界の額で阿良々木とお前、どちらか1人だけの命が助かるとなったら、お前はどちらを選択するのだろうな。
まぁまぁ。
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
さて、自問自答だ。
戦場ヶ原と阿良々木の為に無償で働いてやるという気持ちはあるか?
かつてのライバルたちが無様に殺されるのを見ていられないという気持ちは、俺にはあるか?
Noだ。
絶対にない。下手をすれば俺はスッとしてしまうだろう。
ならば千石撫子という奇病にかかってしまったらしい娘のためなら、俺は無償で何かができるだろうか?
Noだ。
誰だそいつは?知らん。
ならばかつて騙した純情な娘である戦場ヶ原に償いをしようという気持ちを元にすればどうだ?
ライバルではなく旧知の間柄として、戦場ヶ原個人に対して、あるいは戦場ヶ原家に対して何かしようという気持ちなら俺にはあるか?
Noだ。
そんな気持ちなんてない。その件について俺はなんとも思っていない。
例え俺の詐欺の結果、一家の娘が身売りするハメになったところで俺の生き方は1ミリも動かないだろう。
だったら阿良々木はどうだ?そう、あいつの妹を虐めた事があったな。
それに影縫から金をせしめる為に、あいつの情報を売った事もあった。
そのささやかなお返しとして、つまりお釣りとして奴の命を助けてやるというのはどうだろう?
Noだ。
例えお釣りがあったとしても、いくらなんでも割に合わない。
ここまでの交通費でそんなものは消えている。
あとは、そうそう、羽川という娘か。
友人の為に海外に行くという度を越した健気さに心を打たれてみるというのはどうだろう?
あるいは、その娘はとんでもないお金持ちかも知れない。
礼はそいつの両親からせしめるというのは?
Noだ。
うん、駄目だ。いくら考えてもこの仕事を受ける理由が見当たらない。
何の得もないどころか受ける事が俺の損にしかならない。
あぁ、そうだ。そういえばあの街にはいたのだった。
臥煙先輩から見て姪にあたる、つまり臥煙先輩の姉の臥煙遠江の忘れ形見とも言うべき一人娘がいたのだった。
確か今は苗字が変わって神原駿河。神原駿河は直江津高校の生徒で、しかもかつて戦場ヶ原とは仲が良かったのではなかったか?
俺が阿良々木と初めて遭遇したのはその神原家の前だった。
阿良々木が神原と繋がりがあるのだとすれば、当然のように戦場ヶ原と神原も繋がりがあると見るべきだし、
仮になかったとしても少なくとも神原と阿良々木が繋がっている事は確かだ。
神原駿河のためなら、憎き戦場ヶ原と阿良々木を助け千石撫子を騙すことが俺にはできるだろうか?
Yesだ。
【第22話 ひたぎエンド 其ノ貳】
引き受けよう、戦場ヶ原。
お前の依頼をだ。他に何がある。神様騙し、やってやろうじゃないか。
正気だ。とりあえず即金で払えるという10万円を寄越せ。
いいだろう。この額でいい。
これでいいと言っているんだ。
俺が本気で仕事に見合うだけの額を請求すれば、お前が身売りをしても足りんよ。
どんな過酷に働いても足りん。
この10万円もあくまで必要経費として受け取っただけだ。
もしも使いきれずに余ったら…そこまで俺も細かい事は言うまい。
その恩くらいは受け取ってやろう。
この条件以外では俺は引き受けない。
残りの日数が74日というのは間違いないのか?
絶対か?絶対に確かか?
例えば神様が短気を起こして、今日のこの瞬間にお前が殺されるという事はないのか?
どうして?
極端な話、お前は、そして多分阿良々木もだろうが、こうして俺に相談するなりなんなり、
自分たちが生き残る為の策を練っているのだろう?
それは神様の心象を著しく害する行為のはずだ。
向こうが怒って期限よりも早くお前達を始末しにかかるという可能性はどうしたって否定しきれないはずだろう?
お前、お前達、いったいその千石撫子からどんな恨みを買ったんだ?
いったい何をして殺されるところまで行ったんだ?
おいおい、わからないって事があるか。
また羽川か。
低俗な話だな。
ま、いいだろう。それだけ聞けば十分だ。
しかし今回は例外という事で良いんだろうな?
だから、お前達の街に入って良いんだろうな?ということだ。
ふん、そうだな、まぁ俺も奴には会いたくない。
よし分かった。今日からすぐに調査に取り掛かる事にしよう。
そうは言っても戦場ヶ原、1日2日で解決すると思うなよ。
それでいい。信じるな。疑え。
お。
飛行機で今日中にお前たちの街まで乗り込むわけだが、便はお前と別のものにしておいた方が良いだろうな。
お前と一緒に飛行機に乗っていたという事実を、阿良々木にでも知られたら本当に洒落にならない。
なんだ?
着いたぞ。
あぁ。
俺はまず、いきなり本丸からこの件に切り込むことにした。
この件の本丸とはどこか?1つは北白蛇神社だろう。
しかし、さすがにのっけからそこに乗り込むのは無謀を通り越して愚かである。
とするともう1つの本丸だ。そちらが先だ。
本丸が2つも3つもあるのはおかしい気がするが、ともかくもう1つの本丸とは千石撫子の家である。
準備が終わったところだ。これから行動に移る。
なんだか後ろが騒がしいな。三が日からお前どこにいるんだ?
微笑ましい事だな。
千石撫子の住所が知りたい。携帯メールで教えてくれ。
俺は千石撫子の同級生の父親を名乗って、つまりは騙って千石ハウスの中に入った。
うちの娘も3日前からい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んです。
直前に何かお宅のお嬢さんの事を言っていたような気がするので、それが気がかりで非常識にも押しかけてしまいました。
お嬢さんの話を聞かせて頂いても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うんぬん。
娘の撫子さんの名前を出したら、両親は見知らぬ来客に対する警戒心を完全に失ってしまった。
だが、千石夫妻は娘の事を一切、一切合切何も知らなかった。
人見知りだったとか、おとなしい子だったとか、よく笑う子だったとか、そんな事を言っていたような気もするが、
俺が知りたいのはそんな子煩悩のセリフではなく、彼女の抱える心の闇だったのだが、そんなものは彼らも知らないらしく、
しかも知りたくもないようだった。
そして俺は娘さんの部屋を見せてもらっても構わないでしょうか?と言った。
娘が撫子さんに貸していた何々があるはずで、それが2人を探す上で手掛かりになるはずなのですが、心当たりは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ょうか?
というところから始めて30分くらい遠回りをした挙句にようやくそのゴールまでたどり着いたのだ。
子供っぽさや可愛らしさを無理やり押し付けられている様な部屋だという風に、むしろ俺は思った。
先ほど千石撫子の父親が、娘には反抗期がなかった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を言っていのを合わせて考えると色々と思うところはある。
ひょっとするとこの辺りが鍵なのかもしれない。
千石撫子の心の闇。
なるほど、これが千石撫子か。子供っぽくて可愛らしくて気持ち悪い。
なんだか作り物めいていた。
プリティであることを強要されているかのようだと思った。
笑顔は浮かべているがどこかぎこちない。
前髪を下ろして人と目を合わさないようにしている。
というか、もっと言えばオドオドしているようにも見える。
彼女は何に怯えているのだろう?何に?
1人で写っている写真ばかりですね?私の娘とは写真を撮ったりしなかったのかな?
聞いてみると案の定、千石撫子からそう言われているとの事だった。
この時の俺の気持ちを説明するのは難しい。だから事実だけを記そう。
ようするに千石撫子の両親は、自分の娘が行方不明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に部屋を綺麗に、元通りに保つ事だけに執心して
ひょっとしたらそこに重要な手がかりがあるかも知れないのに娘の言いなりになって、
部屋のクローゼットを開けさえしていないという事だった。
千石撫子の写真を送ってくれ。
会ったこともない女なんでな。
俺の間接的な被害者だなんてお前が言っているだけだ。
よく考えたらそれが本当かどうかもわからん。
千石撫子の家でアルバムを見た。
可愛らしい子じゃないか、お前の嫌いそうな。
お前住所を知っ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は千石家を訪ねた事はあるのか?
阿良々木の妹は知っているのか?自分の兄が今陥っている状況を?
だから何者なんだ?羽川。
それより俺はこれで千石撫子の家庭事情の片鱗のようなものを知りはした訳だが、
戦場ヶ原、実際のところお前は千石撫子をどう思った?
情報提供というより雑談のつもりで言ってくれ。
さっき、嫌いなタイプとは言っていたが、何と言うかもう少しエピソード交じりの感想を聞きたい。
ん?どうした?
何?そうなのか?
そうか、なんとなく分かってきたよ。
お前の置かれている訳の分からない状況ってやつが。
欲正気を保っていられるなお前。
ま、俺に助けを求めるくらいだから、お前は案外既に正気ではないのかもしれないがな。
とりあえず、俺はこれから千石撫子に会ってこようと思う。
北白蛇神社に行けば会えるんだよな?
阿良々木は今日は来ないな?神社の境内で鉢合わせなんて御免だぜ。
まぁ、会えなきゃ会えないでもいいんだ。
とりあえずは現地を見てみないと話にならないというだけでな。
全然。
ただ一応ご機嫌伺いというか、顔を繋いでおく程度のことだ。
それに案外、話し合いで解決できるかもしれないしな。
ふぅ。
おじさんと言うのを辞めろ。俺は貝木泥舟という。
考えてみればこれは失敗だった。
千石撫子は俺のこの街で行った詐欺の間接的な被害者である。
ならばどこかから、阿良々木や、ファイヤーシスターズから俺の名前を聞いていてもおかしくはない。と思ったのだが。
きっと俺の名前を聞いていて知っているはずだ。
しかし、それをもう覚えていないのだ。
この娘は、自分をこんな状態に追い込んだ諸悪の根源を今となっては忘れている。
そういうことだと思った。
忘れられないようなことを普通に忘れるのだ、こいつは。
その代わり、どうでもいいことを、例えば子供の頃友達のお兄ちゃんに優しくしてもらった事とかをいつまでも覚えている。
つまり、物事の重要性の順序が、この娘の中ではしっちゃかめっちゃかになっているのだと、俺はそう理解した。
そうだな、約束を守るというのはとても大切なことだ。崇高と言ってもいいかもしれない。
俺はそんな心にもない事を言って話題を合わせる。
この娘がとても哀れに思え、否定するようなことを言え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だ。と思ってくれていい。
来客、というか参拝客にはしゃぎ、楽しんでもらおうと面白い話をする中学生のような神様が滑稽で哀れでしょうがなかった。
同情せざるを得なかった。
宣伝が足り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あるいはサービスが足りないとか。
何をやっているのだあの男は。
なぁ、と、お前、お前はその暦お兄ちゃんか?
暦というのが苗字なのか名前なのか知らないが、お前は暦お兄ちゃんの事が好きなんだな?
そうか。
なぁ神様、お前人間に戻れるとしたら、戻りたいか?
人間に戻ったら暦お兄ちゃんと恋人同士になれるとしても?
そうだな。
暦お兄ちゃんは何度もこの神社に来ているのだろう?
それはお前参拝客、お客さんには含めていないのか?
他には本当に誰も来ないのか?
暦お兄ちゃんと俺以外には今まで本当に誰も来たことがない?
皆がお前を見て逃げるのはお前の姿が不気味だからだろう。その髪は怖すぎるぞ。
この子にとっては可愛いとはもはや誉め言葉でも言われて嬉しい事でもないのだ。
むしろその言葉で多くの行動を制限されてきたのだろう。
だから、侮辱のような、ともすれば悪口が一周して嬉しかったりするのだ。
確かに、確かにそれならば人間に戻らず、このまま神様を続けている方がこの子のためではあるのだろう。
それを思うと気が重くなりかけたが、しかし例えそうでも、俺には全然関係がない事に気付いた。
遅くなってきたから俺はそろそろ帰るぞ。
暇なんだったらこれで遊んでおけ。
なんだ?知っているのか。
いくつか技を教えてやる。
お前がそれを極めるまでにはまた来てやるさ。
本当だ。
俺は嘘を吐いたことがない。
正直に俺はそう言った。
そして白々しく、あるいは腹黒く続けた。
なにせ俺はお前の信者第1号だからな。
【第23話 ひたぎエンド 其ノ參】
えぇ
仕事の報告だ。まだ電車が動いている内に、戦場ヶ原、ちょっと出てきてくれるか?
会って話したいことがある。できるだけ早くだ。
ははっ、そりゃいいな。
そうだな、少なくとも生意気なガキが身の程をわきまえて従順に首を垂れる姿は見ていて悪いモノではないな。
そういうお前はどうして夜なのに制服を着ているんだ?
この辺りにファミレスはあるか?
俺はかなり野暮で世間知らずな男だがな、レディをエスコートする時には当然店の予約をする。
だから今はしていない訳だ。
奢ってやってもいいぞ。
だったら今すぐ機能の飛行機代を払えよ。
そういえば喫茶店での飲み物代も結局俺が払ったんだったよな?
お前、もう少し後先考えて発言した方が良いんじゃないか?
どうせそんな風に考えなしに千石撫子とも話したんだろうよ。
お前、なぜその暑そうなのを脱がないんだ?
脱げよ、鬱陶しい。
いっそ、阿良々木に正直に話してしまえばいいんじゃないのか?
お前が懇切丁寧に感情的にならず理論立てて説明すればそれでも嫌がるほどのわからず屋でもないだろう。
誤解?
そりゃあ悪かったな。
お前は俺に騙されていいように弄ばれただけなのに。
なぁ戦場ヶ原、1つ聞きたいのだが。
お前こういう風に食事をしている際、席を外すときに鞄を持って行くか?
俺を想定するな。
そうだな、たとえば今日お前は阿良々木家で正月を祝ったということだが、その時俺との電話で廊下に出る時、自分の鞄を持って出たか?
ふん、まぁそうだろうな。
いや、千石撫子はそういう時にちゃんと鞄を持って出る奴だったんだろうな、と思って。
それが今日俺が千石撫子に会っての感想なわけだが。
俺は、偽物だよ。知ってるだろう?
あいつは誰も信用することなく、誰も信じる事もできず、13年だか14年だかを生きてきたんだろうな。そう思った。
もしも本当にそうだったのならこんな事にはなってないさ。
まぁその件に関しては阿良々木が悪い、釈明の余地なくな。
ぇあ?俺がか?
この件で真摯に謝られると逆に不愉快だ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が、
なぁ戦場ヶ原、あの娘千石撫子が同情を誘う環境にある事は確かだったよ。
俺も同情くらいはしたよ。
しかしそれは昔の話であって、今は割と楽しそうにやってるみたいだし、どうでもいいだろう。
戦場ヶ原、とりあえず安心していい。
あの娘を騙すのは容易い。
まぁお前には無理だよ。阿良々木にも無理だ。
だがそれ以外の人間なら、俺でなくとも可能ではあると思うぞ。
千石撫子、あいつは馬鹿だ。
多分愚かさや稚拙さをずっと見逃され続けてきたのだろう。年齢以上に幼い。
俺はこれからあの神社に通って、千石撫子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取りつつ信用を勝ち取りながら、
そして来月くらいか、お前と阿良々木が交通事故にでもあって死んだと伝える。それで解決だ。
確認しない。あいつは確認しない。そのまま鵜吞みにする。
話してみりゃわかる。
ありゃ、甘やかされ過ぎていて、甘えすぎていて、他人が自分を騙したり嘘を吐いたりすることを基本的に想定していない。
人を信じられない代わりに、人を疑う必要もない。そういう環境で育っている。
俺が半年前に仕掛けた詐欺の間接的な被害者だということだが、
しかし、本人は案外ひょっとしたら何かの間違いだと思っ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
自分がそんなおまじない、呪いの対象になるだなんて。
まぁとはいえ、失敗した時のリスクを考えるとやっぱりチョロい仕事だとは言い難いがな。
万が一にも看破されたら俺は生きてはいられないだろう。
悪意に鈍いからこそ、だからこそ、ちょっとした悪意や、普通ならば感化できるような害悪を、きっとあいつはスルーできない。
千石撫子がお前に拘泥しているのは逆に言えばその程度の気持ちでしかない。
千石撫子は神様化することでむしろ幼児化しているようだ。
そう、生まれ変わったとでもいうのかな。
案外あいつは良い神様になるんじゃないか?
勿論神様としての威厳を出す為には、もう少し落ち着きが必要だろうが。
だから安心しろ、凡そお前たちは助かった。
良かったな。死なずに済むぞ。
春からは花の大学生というワケだ。
好きなだけ阿良々木とイチャつけるぞ。爛れた生活を送れるぞ。
まぁ問題は阿良々木に、事が解決したというのをどういう風に伝えるかということだよな。
あいつがしているという誤解を思うと、俺が正直に千石撫子を騙したとは言えないだろうし。
何の真似だ?俺に奢られるのは嫌なんじゃなかったのか?
変わった基準だな。
ん、いい方法があるぞ。阿良々木に私と千石撫子、どっちの方が大事なのよ?と選択を迫るんだ。
お前がそういう鬱陶しい女になればあいつはさすがに千石撫子を諦めるだろうぜ。
戦場ヶ原ひたぎはようやく気を緩め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だろう。
無論、それでも自分の事だけだったのなら意地を張ってあの女は泣かなかったのかも知れない。
だが恋人の命まで助かったとなれば、泣かずにはいられなかったのだろう。
そういう女だ。そういう馬鹿だ。
厄介なのは経費の方かな。
1度会う度に1万円とか必要経費の残金じゃあと5回も会いにいけないぜ。
よーし覚えた。
お兄ちゃんなどという呼び方はするな。
影縫のやつはどうした?ひょっとしてこの辺りに来ているのか?
秘密?
しかし、そうは言ってもお前は影縫の監視役だろう?
斧乃木、お前は一体何をやっているんだ?
臥煙?
いや、待て、聞きたくない。言うな。
手を引け?
最後のは臥煙先輩が言ったのか?それともお前の最近のキャラか?
そうか。今度言ったらブッ飛ばすからな。
何か追加で飲みたい物はあるか?
人を阿良々木の様だと侮辱しておいて、奢ってもらえるとでも思うのか?
ふん、臥煙先輩は俺の事を分かっているようで案外分かっていないな。
困ったもんだ。手を引けなんて言われたら俺はむしろヤル気を出すに決まっているだろう。
お断りだな。あまり人を安く見るな。桁が1桁は違うんじゃないのかと伝え返せ。
ん゛。ん。
さぁてどうだったかな?
ふーん。
ふーん。
俺は考える。
さっきも1度考えたが、さっきよりも深く考える。
夕べ見た戦場ヶ原の泣きはらした顔、そしてお礼の言葉を、他でもない俺に対して言ったお礼の言葉を思い出す。
それから臥煙先輩との関係、利害関係。300万円という提示された額を思い出す。
斧乃木、わかった、手を引こう。
当然手を引くつもりなどなく、俺は斧乃木から300万円を受け取ってからそのままその足で北白蛇神社へと向かった。
無論、その代償として臥煙先輩を敵に回してしまったが、考えてみれば元々敵みたいな人だったので
むしろこれで縁が切れてさっぱりとしたような気分だった。
そりゃまぁ、お前の信者第1号だからな。
実は俺には凄く凄く叶えたい願いがあるんだよ。
だからこの神社にお百度参りってやつをすることにしたのさ。
さぁて、一言では言いづらいのだが、まぁそれでも無理やり一言で言うならば商売繁盛ってところかな。
まぁこれから100回、厳密に言えばあと98回俺はここに来るんだ。慌てる必要はない。
追々話していくさ。
あやとりねぇ。いいだろう、昨日やったあやとりを出せ。
んぉっ。
この娘は馬鹿で、しかも狂っている。
頭が悪く頭がおかしい。
尾行されているなぁ、と気付いたのは山を降りそれからしばらくしてからの事だった。
1番可能性があるのは当然臥煙先輩の下っ端という線だ。
で、次に高いのは俺に恨みを持つ中学生かな。
ただその場合、いきなり後ろからどつくなりなんなり、直接的な暴力に打って出そうなものだ。
えぇ、まぁ。
楽しいですね。色々スリリングで。
結局タクシーで送ってもらった駅から電車に乗ることもなく、ホテルに戻ることもなく
そのままトンボ返りで俺は元の街に戻った。
尾行を警戒したのではない。それはもう完全に気にするのを辞めた。
それよりも気にするべきことがあった。千石撫子の壊れ方だ。
失踪した娘の手がかりのようなものが見つかった。
電話で話せるようなことではなく、あなたたちの判断もお聞きしたいので今から言う場所に来て頂けないか?というような事を
とても遠回しに、つまり遠慮気味に、しかしそれなりの断りづらさを織り込みつつ俺は言う。
さーて。
なんだこりゃ?
轉自:https://4threich.blog.fc2.com/
#三木真一郎 #貝木泥舟